诺维家衣柜-广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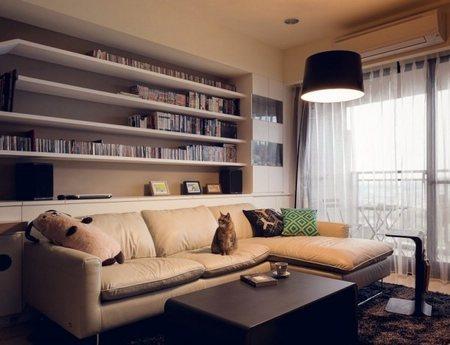
2023年9月22日发(作者:乌力吉)
吕世浩:我的学习历程──永怀师恩
展开全文
很荣幸也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谈谈我的学习历程。作为一个
历史人,有时候反而是自我的历史最难讲得好。在这里,仅能就我求
学过程的一些经验和感受,希望藉此机会提供读者们参考。
我是在1991年进入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大学部就读的,进台大是我
长久以来的梦想。但为什么当年会选择历史系呢?这大概和我小时候
一件偶然的事情有关。
我从小就喜欢看书,喜欢看各式各样的书,包括自然百科、人文
图书,甚至是小说、漫画。但小时家中贫困,没什么钱买书,为了在
书店白看,或是向别人借书,遭到白眼相待,是常有的事。在我小学
二年级时,一次陪母亲去市场买菜,途经一家小书店,在我央求之下,
母亲终于答应让我买一本20元以下的书。还记得当时一 本最便宜的
《机器猫小叮当》漫画,定价都要25元,最后我挑了很久,终于才在
店中找到一本20元的书,那是一本文白对照的《古文古事》。此书陪
伴我多年, 反复阅读。如今回想,大概从那时开始,就种下我对古代
史和文言文的兴趣吧!
进入台湾大学后,我遇见了许多好老师,或学养深厚,或豁达大
度,或平易亲和,或热心助人。举个印象深刻的例子来说,在我大四
那年,有位马来西亚的侨生同学,本来已经高兴的考上了研究所,却
国学基础,甚至每晚到校外书院听课学习。而正因为阮老师的严格,
这段时间成了我进大学以来成长最为快速的时期。还记得考上硕士班
后,我拿了自己的一篇论文去请老师教正。结果两天后,阮老师把我
找去他家里,从题目名称开始骂,一直骂到结论,文章上密密麻麻全
是老师批改的字样,足足骂了我一上午,然后要我拿回去改,改好再
来找他。过了几个月,我把老师交代要看的书都看了,论文也改好了,
再去见阮老师。 老师又看了两天之后,再找我去骂,这一次骂了两个
多小时,一样批改无数红字,要我回去改好再来找他。就这样,我硕
士班的第一篇文章足足被骂了五次,改了将近两年,阮老师才终于点
头说:“可以了,这篇文章合格了。”这就是我后来读博士班一年级
时,发表在《燕京学报》新九期(2000年11月)的《三王与文辞 ──
史记·三王世家》析论〉一文。
《燕京学报》是极为严格的期刊,能够以学生的身分在上面发表
文章,对当时的我是莫大的鼓励,也坚定了我日后走向历史研究道路
的信心。看到现在很多在硕士班就大放异彩的年轻同学们,我常觉得
自己并不算是天资卓异的人,能够有今天,都得拜老师的严格教导之
1998年硕士班毕业后,我曾有一年的时间担任阮老师的专任助理。
就在那一年,我遇见了改变我一生的第二位老师,也就是徐苹芳先生。
徐苹芳先生是众所公认中国考古学界的第一流学者,他曾在1999年接
受本系的邀请,来系上担任一学期的客座教授,徐老师和我的初识便
是在台大客座的这段期间。由于阮老师常常鼓励我多听其他老师的课,
而他对徐先生之为人与为学一向推崇,因此素来仰慕先生的我,便立
刻把握机会前去旁听,从此启发了我对于中国历史考古学的认识。
接触过徐老师的人都知道,先生待人极为温和谦逊,但在学术上
却非常严谨认真,因此上徐老师的课是一点也不轻松的。先生当时开
的课是《中国考古学》,整个学期分为十多个专题讲授,全面而深入
的介绍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成就。先生上课没有讲义,没有
PowerPoint或其他花俏的教材,有的只是长篇的参考书目和极为精彩
而充实的授课内容。先生博学多闻,又长期在第一线进行考古工作,
上课内容除了丰富的考古知识外,还融入了许多个人长期从事考古工
作的体悟。上课从钟响开始,便如行云流水一般接连讲授。当时在讲
台下的我,唯恐漏掉任何一句,只能奋笔疾书,拚命抄笔记。第一次
听完先生的课后,印象最深刻的是那酸痛的手指,和满是开启另一扇
学术之窗的兴奋之情,心中想到的只有当年孙中山初次赴美后的那句
感言:“今日始见沧海之阔!”
徐老师和阮老师相同,除了学术研究外,更重视后进的品德修养。
前面提到,我曾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三王与文辞》投稿到《燕京学
报》,其实我原本想投到《台大历史学报》,但阮老师当时正好担任
主编,因此立刻要我回避。《燕京学报》是学界公认的第一流学术刊
物,当时贸然投稿,只能说年少的我血气方刚,初生之犊不畏虎吧!
结果过了半年多以后,大约是徐老师来台后的学期中,有一天先生忽
然约我见面,见面后和我谈这篇稿子,我才知道原来当时担任《燕京
学报》副主编的正是徐先生。
徐老师对我文章的论点十分赞许,但指出文中对前人的错误往往
多加指摘讥刺,这样的态度是不宜的。先生对我说,前人的错误往往
根源于时代的局限性,错误固然要讲清楚,但心态应该宽容,不宜过
多苛责。我年少家庭穷困,因此心中愤世嫉俗,但先生的那一番话确
实点醒了我,促使我开始思考用另一种态度去看待世事。更让我感动
的是,先生当时和我足足谈了一下午,理直而气和,义正而辞婉,苦
口婆心,谆谆教诲。
我常想,我的人生中最幸运的事就是能一直不断遇上好老师。以
阮老师和徐老师的学识和地位,他们大可不必花如此多的时间,在像
我这样没有背景、没有渊源的穷学生身上,但他们却如此做了,而且
始终如一。在两位老师的身上,我看到了学者不遗余力栽培后进之心,
这也真正感动了我的心。
徐老师在学术上的毕生愿望,便是能将历史学与考古学加以结合。
他所以在历史学系开授考古学课程,也是这个用意。因此先生当时和
我谈论那篇稿子,更希望我能结合出土文献和考古成果,让论点更加
坚实。先生当时帮我开了一连串的汉简书单,特别是迈克尔·洛伊
(Michael Loewe)和永田英正的书,要我细心阅读。先生当时跟我
说,年轻人要厚积薄发,我由《史记》研究跨足汉简和考古,固然会
使文章发表时间要延迟许多,但对我的 将来绝对是有益的。后来我足
足花了半年多的时间,阅读了相关书目(尤其是迈克尔·洛伊的原文书,
硕士班时,选择了阮老师最擅长的《史记》,做为论文题目;而既然
想学考古,我就希望学到如何正确使用第一手的出土史料,而不是只
能仰赖阅读考古学者的二手研究。所以当时我立志排除万难,必要到
中国考古最好的大学去学习,并参与完整的考古发掘工作。
要做这样的决定,在当时有许多难处。主要是我在经济上很不宽
裕,而除了旁听和修习过人类系的几门课外,更非考古科班出身。但
当时的我,不断想起小时候在《古文古事》中读过的一篇故事:蜀之
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
如?」富者曰:「子 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钵,足矣。」富者
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贫
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西蜀之去 南海,不知几千里也;
僧之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焉。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
再怎么没钱,我想我都比“一瓶一钵”要强,“有为者亦若是!”
就这样,我下定了要去北京大学学习考古的决心。
徐老师唯恐我受学界浮躁的风气影响,有急于求成的心态,当天
中午请我吃饭,就认真告诫我:“世浩,你做我的学生,我只要你答
应我一件事,那就是一辈子不许 写和人商榷的文章。”后来我才体会
先生的深意,学术贵在正面立论有所贡献,不在找人毛病以为高人一
等。还记得那一天,先生屡次的跟我说:“世浩,要切记, 大器一定
要晚成,厚积才能求薄发。”
徐老师十分喜好美食,时常带许宏师兄(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和河南偃师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和我
去北京不同的名菜馆尝鲜。在轻松的气氛下,不断关心着我们的学术
和生活情况。席间先生总要我谈谈对大陆的各种感想,有时年轻的我
忍不住大放厥辞,先生总是面带微笑认真听我讲完,然后一一对我的
产生重大影响,是在北京等大城市生活绝对无法感受的。
2002年,因为我的毕业论文实习,需要用到大量未发表的悬泉置
出土汉简,徐老师特地亲自陪我到兰州的甘肃省考古所去。还记得当
晚在房间聊天,谈起先生刚故世的好友,也是国际知名学者张光直先
生发掘商丘的事。先生提到他原本建议张光直先生合作发掘的地点是
河南偃师二里头,因为他觉得那里最有考古潜力,也最能做出惊人的
成绩。以2001年后二里头丰硕的考古成果来看,先生的看法无疑是无
私而正确的。但张光直先生当时不同意,坚持要发掘商丘,先生力劝
无效,而最后发掘的结果并不理想。先生说起此事时十分怅然, 因为
张先生与他多年朋友,却因此而生嫌隙。但先生对我恳切的说:“我
不能害朋友去做一件明知没结果的事。”这让我学习到先生对朋友的
情义。
在甘肃实习期间,我幸运的获得了曾参加居延新简整理工作,并
主持敦煌悬泉置发掘的何双全老师的细心指导。在那三个月里,何老
师不仅作为我学习简牍和考古的良师,他和师母对我这样一个异乡游
子,更像亲人一样照顾,至今感念不忘。后来因为何老师的引介,我
还参加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简牍研究班的敦煌居延考察旅行,
更令我大大开阔了视野。
波折和坎坷,时时心存感谢。徐老师常教诲我应与人为善,先生说他
的一生常因此而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受人帮助。当先生故去的消息传到
台湾,就我亲身耳闻目睹,认识先生的学者,无论社会地位、政治立
场、学术派别,无不感怀伤痛,在今日多元的台湾,这是何等难得之
苏州邻瑞广场-沪深股市今日涨幅排名一览表

更多推荐
东四二手房








发布评论